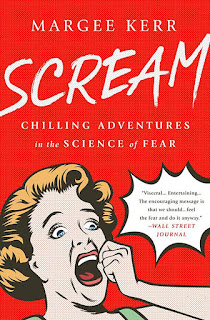〔繼續聽審,繼續要有感想。〕
早前受蔡元豐教授之邀,為友校浸大中文系系會學術周作一演講。學術周主題為「女性書寫」,不知哪來的勇氣,我把題目訂為〈從冰心到黃碧雲——中國女作家一百年〉。這題目乍看真箇溫柔與暴烈,風馬牛不相及,不怕得罪冰心也怕得罪黃碧雲;其次,所謂「中國女作家一百年」也有點托大,一小時演講如何說起;再其次,也沒有再其次了,但我就是想說,女作家一百年走過的路徑,比我們想像的相似。一切從冰心(謝婉瑩)〈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〉說起。
王德威教授曾說過冰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張「乖乖牌」,二十世紀再漫長暴烈,政治戰火風雲激盪,至少我們還有冰心。在啟蒙理性的五四精神裏,她歌頌母愛的〈致詞〉提出一種超越生死的基督大愛「萬全之愛無離別,萬全之愛無生死」;在敵我分明的歷史時刻,她寫小說〈超人〉,以母愛聯繫全人類︰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,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,都是互相牽連,不是互相遺棄的。」即使留學美國,也要手摺紙船,向母親寄託無邊思念︰「母親,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,/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。/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著淚疊的,/萬水千山,求他載著她的愛和悲哀歸去。」
但冰心也很坦白地說︰「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,把我『震』上了寫作道路。」五四運動,是青年學生不滿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對中國各種不平等條款,以示威、遊行、請願、罷課、罷工反抗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的運動。冰心就是因為五四運動而走上成為現代文學「乖乖牌」之路。冰心呼喚著「母親啊!你是荷葉,我是紅蓮,心中的雨點來了,除了你,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?」而她心中的雨點,包括學生運動,她的寫作起點,也是學生運動。
乖乖女冰心發表的第一篇文章,是1919年8月25日《晨報》上的〈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〉,下署「女學生謝婉瑩投稿」。所謂「二十一日」的審判,是8月21日北大學生案公判。事件可謂五四運動的餘波,關係到擁護蔡元培校長與胡仁源署理校長的兩派學生之爭。其後演變為擁胡的四名學生為原告,控告十一名擁蔡的學生拘禁、毆打、迫寫悔過書等罪狀。五四過後不久,北大學生對簿公堂,其中被分化與變質之感,以及面對囹圄之苦,莫不令人惋惜。冰心是其中一人。她作為女校學生代表,在旁聽席上記錄了大多數群眾對十一名被告的招呼與慰問,並認為他們「自有榮譽」;四名原告則是「心死的青年」。
` 文章發表前三日《晨報》已有較詳盡的新聞報導,因此冰心所述確為「感想」,包括審判廳內「不准吸煙吐痰」,「但是廳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。」又劉崇佑律師為被告辯護時「沉痛精彩」,「有一位被告,痛哭失聲,全堂墜淚。」查劉崇佑的辯護確實精彩,據《晨報》二十二日的報導引述︰「此案之發生,社會上誰不知係受政潮之影響。使非因有欲爭校長之人,則學生內部何至有此種事件發生。此輩青年不幸而為中華民國之學生,致欲安分求學而不得,言之實可痛心……語至此滿堂欷歔為之淚下。」旁廳席上的公道,在記者與未來作家冰心的筆下同樣可見。冰心的在聽審八小時後回到家中,寫到鄉下婦女張媽說「兩邊都是學生,可苦這樣」,「學生打吵,也是常事。為什麼不歸先生判斷,卻去驚動法庭呢?」是以張媽的話竟與劉律師如出一轍。
文學理念與立場再溫和的人,心靈也會因公義而攪動,動身或動筆參與其中。女作家往往更在風高浪急之際,在漩渦的中心寫出平民大眾的「公道」與「輿論」。一百年前如此,一百年後亦然。《盧麒之死》終章有被告欄青年的素描,上有案件編號、中英文名字,以及女作家的敏感︰「他說很倦。我在夜之深靜默。」「他沒有我畫的那麼文靜。但我畫的時候,想起你的髮。」這種情感釋放的自由,我很珍惜。「他」說很倦,「我」在夜之深靜默,就是同情共感。
〔原載2021年3月9日《明報》世紀版〕